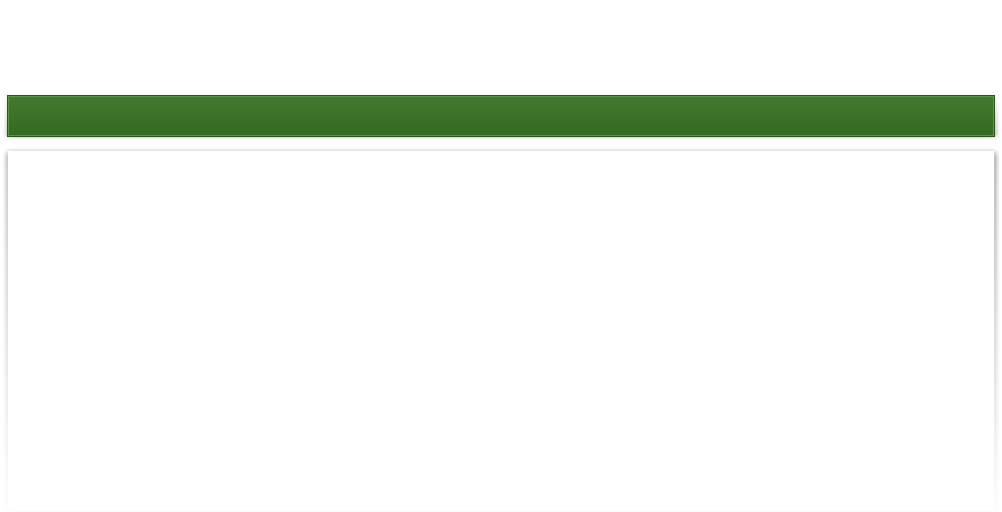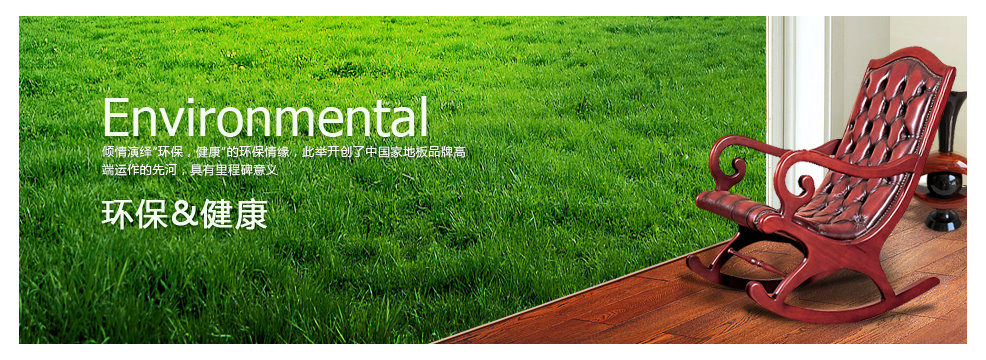每次回到老家,我总会往菜市场的小吃店里钻,点一份豆芽菜炒粉皮,或是绕到永兴大道那家老店吃猪杂粉。手工炊出来的粉皮,厚度适中,软滑中带着嚼劲,轻轻一嚼,弹滑的质感在舌尖散开,混着汤汁的鲜香,一口下去,满是熟悉的暖意。
以前,堂大姑是做手工粉皮生意的,我时常去她家里和她的女儿们玩,自然而然的,我也就见识过堂大姑做粉皮。做粉皮的头道工序,讲究一个“泡”字,前一晚就得把大米浸泡在清水里,让米粒吸足水份,变软,隔天一早,便把泡好的大米捞出来,连水带米倒入碾米机里面,随着“轰隆”声响,米粒在里头被磨得粉碎,不一会儿,乳白的米浆顺着出口汩汩淌出来,流到水桶里面,乳白的米浆绵密得像牛奶般。
接下来便是关键的一步——炊粉皮,簸箕里面铺上一张沙布,扫上花生油,用勺子搅拌水桶里面绵密的米浆,倒入两三勺米浆入簸箕里面,拿起簸箕,上下左右晃动,使米浆均匀地铺满整个簸箕,然后,把簸箕放进沸水翻腾的灶锅里面,盖上锅盖,蒸两三分钟,出锅,再放另一个盛有米浆的簸箕入灶锅里面蒸,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粉皮,大米香味极其浓郁,洁白的颜色像雪一般诱人。最后,提起放凉黏着沙布的粉皮,倒铺入另一个簸箕里面,沙布与粉皮揭开分离即可,如此重复,炊出一张张洁白的粉皮。粉皮炊好之后,便是切粉皮,把一层粉皮对折起来,放到粘板上面,用刀切成一条条,再放入箩筐里面码起来,即可挑到菜市场售卖。
有一次,奶奶把堂大姑给的粉皮装到簸箕里面,拿到阳台上晒,经过几天炽热太阳光的烘照,原先洁白又软乎乎的粉皮,变得透明干硬,像极干粉条。晒干后的干粉皮,奶奶把它加上猪瘦肉煮上一锅猪瘦肉干粉皮汤,出锅前放上一些葱花和调味料即可。奶奶盛了一碗给我,我用筷子夹了一撮干粉皮送进嘴里轻轻一嚼,嚼劲、爽滑和干粉皮吸收着猪瘦肉汤的鲜甜,缠成一团,美味可口,我就这么一口接一口地吃,根本停不下来,不知不觉已吃了两三碗,嘴上还沾着汤汁的油光,奶奶见我吃得这么欢,脸上的纹路都笑出了花朵来。
小时候,在小吃店里,粉皮只有两种简单的吃法。一种是用热油爆香蒜蓉,将粉皮倒入热油锅里清炒几下,临出锅时淋勺酱油调色,装盘,粉皮炒得软乎乎的,十分鲜香;另一种更省事,直接把装在碟子里面的粉皮浇上蒜蓉酱油调料,用筷子搅匀即可食用,蒜的辛辣混着酱油的咸香,裹着粉皮的凉滑,搭配得恰到好处。这两种味道,至今都让我回味无穷,尤其是粉皮拌蒜蓉酱油调料,简单得没一点花哨,却比任何复杂的调味更让人记挂。
随着人们对饮食的不断精细化追求,粉皮早已跳脱了曾经简单的吃法,如今的花样可比从前丰富多了,有豆芽菜炒粉皮、叉烧炒粉皮和猪肠子炒粉皮,汤粉更是让人惊喜,有猪杂汤粉、牛腩汤粉和胡椒猪肠子汤粉,不管汤或是炒,最终都会化作舌尖上的百般滋味,总能精准地挠到每一个人的味蕾。
写到此处,我的心里头对老家粉皮的惦念又翻涌上来,真想立刻驾车朝老家的方向去,坐在那熟悉的小吃店里面,尝上一碗心心念念的滋味。
本报利用新媒体平台开设“吾乡吾土”专栏,挖掘宣传推介阳江乡土文化,搭建一个阳江乡土文化作品展示和交流的公众平台。现诚邀社会各界乡土文化专家、学者和网络作者赐稿。稿件要立足阳江乡土文化,内容可涵盖自然地理、风土人情、衣食住行、诗词楹联、历史文化、名人掌故等方面,以散文、随笔为主,一般不超过1200字,并适当配以图片、短视频。 稿件内容要求原创,主题健康,积极向上,不得抄袭、套改,谢绝一稿多投。来稿请以电子版本形式发送至邮箱,并注明“吾乡吾土稿件”。稿件一经采用,稿酬从优,请作者在文末附上姓名、工作单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、开户银行支行名称及账号等信息。
下一篇:历史回响:中国手工业的世纪变迁